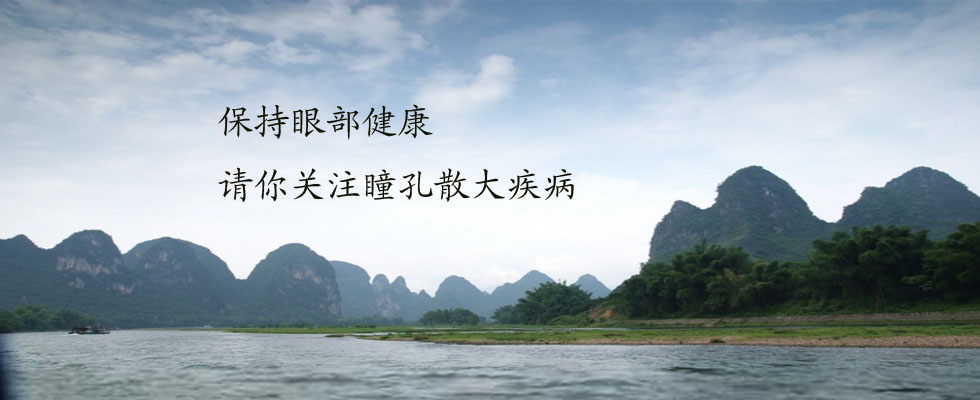一个人一生需要多少张照片?
这不是个问题。这也是个问题。有人喜好照相,一万张也嫌少;有人没此爱好,一张也嫌多。
我属后者。我不喜好照相,也不痴迷收藏照片,无论自己的还是家人的,我都不爱收集整理。因此,我常遭来家人的白眼和恶语:怪古董。
我是“怪古董”,但我有自己的看法。第一,任何东西,一多就泛滥,一泛滥就成灾,一成灾就好事变坏事。数字技术发展,电脑普及,让人人都成为摄影师,人人都成为成百上千张照片的拥有者,如今,有几家不闹“照片灾”的——电脑硬盘塞满,U盘装满,刻录的光盘一大本,可以预见,“照片灾害”还将继续闹下去,生命不止,拍照不止,走到哪儿,拍到哪儿,手机随身拍,数码机专业拍,你拍我,我拍你,不停拍拍拍。
在胶片时代,“照片灾害”还不至于此,买胶片,冲照片,既麻烦开支也不小,很多家庭就三五本相册,有空时翻看翻看,勾起往事回忆,是一种回味无穷的人生体验。现如今不同了,照片实在太多,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翻看起了,就只好不看了,让那些灿烂的笑容美丽的景致藏在数字的世界里吧。说到底,这些照片没人翻看,也就没有人生的回忆了。拍照留恋之目的是给自己和别人看的,多得连自己都懒得看了,照片的意义也就失去了。七年前,我和太太花大力气花大价钱,照了一套婚纱照——甚至当时为一张照片的我没有笑太太还与我争吵一通,搞得浪漫扫地。我印象中,拍照至今的七年里,我们没有再翻看那些照片一次(婚纱照总把自己拍得不像自己),现在不知道它们躲在柜子的那个角落,等待尘埃落满。
关键是现代人还有个毛病,舍不得丢弃也不会丢弃。拍吧,拍得多多的,也没有错,但从需要的角度说,留下来的相片并不需要那么多,那就舍弃一些吧。说到舍弃,很多人一定有这样的经历,积累一段时间后,坐下来准备清理清理照片,可是当鼠标点到这一张时,心想这张说不定留着有用呢;鼠标点到那一张时,心想那张还是留着吧,拍得挺滑稽的……结果,清理到最后,无论是确实值得留下的,还是应该舍弃的,一张也没删掉。其实,这是一种糊涂的人生观通过照片一事的反映。尽管人的年龄和经历在做加法,但我们的生命和需要是在做减法的,学会舍弃,轻装上阵,就是做减法,这与每天都在消逝的生命才是对等的。
第二,任何东西,以稀为贵,一贵就有价值,一有价值就值得留恋。照片也是如此。我爷爷那辈人,照相是一生的奢侈,只有富贵人家才照得起相,碳素画像成为普通人家的选择,活着时为自己留下一张遗像的做法,让碳素画像的生意很是兴隆,并成为一门古老的营生手艺。
我一个本家叔叔就学过这门手艺,只不过当他学会的时候,乡村的小路上出现了走村串巷的照相师傅,他们扛着笨重而神秘的“木盒子”,显得见多识广,很神气。随后,稍稍贵些的黑白照相取代了碳素画像,我那位本家叔叔的手艺还没开张就遭淘汰了,如果说开过张的话,那便是他正儿八经画过一张相,是为自己。他患癌病过早去世,那副碳素画像成为他的遗像,三十年过去了,那张相至今还挂在他家里,偶尔回老家看到,总让我沉默良久,尽管那时黑白照相已经稀松平常,但他拒绝那玩意儿,一辈子没照过一张相片,他留下的唯一影相是自己为自己画的那张遗像。
我最早开始照相,已经是四五年级了。照相师傅隔半年或一年从镇上到村子里来,村子里炸开了锅,一群小孩子奔走相告,像过年。大人不舍得照,主要给孩子们照,照也只照三两张,所以我小时的照片很少,都是小小的,小孩的半个巴掌大,黑白,如果再加点钱,照相师傅就可以给相片另外涂上一层胭脂,变成“彩照”,照片的下面还写有“曙光照相”“晨光照相”等字样及年月日。
我很喜欢看我少有的几张孩童时期照得黑白照片,我很珍视它们,尽管时间久远但画面质量都很好,与一批后来照得彩色照片放在一起,其他都褪色发黄,它们却如二三十年前一样,清晰有质感。我看它们,便是看过去的我,我的感觉挺奇怪的,看照片上幼稚的表情,我觉得那是真正的我自己,而看现在的一些照片,我觉得那不是在看我,像在看别人,照片上的我与自己很是陌生,尽管这些色彩鲜艳、篇幅大大的相片就是不久前专业的相机专业的摄影师拍摄的。
或许还是因为当时的照片少而弥足珍贵吧。也或许,还是因为人是一种怀旧的动物吧。
一个人一生到底需要多少张照片?让我们回到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上来。多了不好,少了也不好,在我看来,一个人一生只需要六张照片,足矣,恰到好处矣,意义重大矣。
这六张照片是:出生时一张,学业完成时一张,结婚时一张,做父母时一张,当爷爷奶奶时一张,去世时一张。这是人的一辈子,这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印记,虽然这些印记会在若干年之后消失,但作为某某人存在过的直接“证据”,聊以供后人回忆和追溯:这是我爷爷,这是我爷爷的爷爷……如果我们的后人连前人的六张照片都嫌多了的话——因为在他们眼中活人的照片多得都无法保存,哪还顾得上逝去的人的照片呢?——那么,一个人一生只需一张照片即可了,就像我的那位本家叔叔,一辈子一张照片,却在一个家族永远挂下去。
现在想来,我比较遗憾的事是,二十年前我爷爷去世时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他的样子模糊得我都想不起来了,当时要是拍一张照片就好了。不过,我的外婆今天还活着,她已经八十八岁了,老得不能再老了,她每次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儿啊,我什么时候死啊!我说:我不是你儿,我是你外孙。我记忆中,她好像是这个“照片成灾”的时代唯一一个没有一张照片的人,无论如何,今年冬天回家,我得当一回摄影师,为她拍下一张照片。
作者简介
石华鹏,年5月出生于湖北天门。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年结业于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级研讨(文学理论与评论家)班。年开始文学创作,以小说、散文、评论写作为主。在《文艺报》《文学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福建日报》《羊城晚报》《文学自由谈》《长江文艺》等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评论余万字。曾获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长江文艺杂志社“旅游散文奖”、江苏省第21届报纸副刊好作品奖、首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新人奖、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等。评论、随笔分别入选《年中国争鸣小说精选》《年中国争鸣小说精选》《最适合中学生阅读随笔年选》等相关年度选本。出版随笔集《鼓山寻秋》、评论集《新世纪中国散文佳作选评》。现任《福建文学》杂志社主编助理、副编审。
福建作家∣ID:fjzjxh
福建作家官方白癜风有什么偏方治疗吗白癜风医院长沙哪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