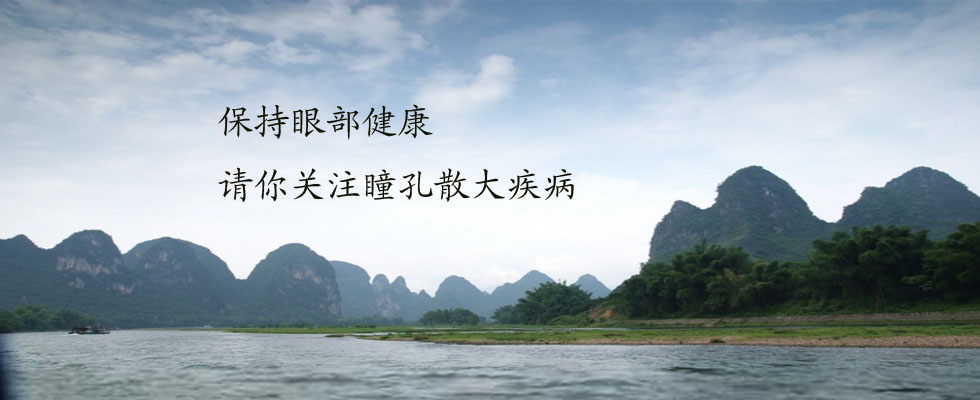17岁的马蒂·坦格列夫(MartyTankleff)发现父母死于长岛家中。他的母亲被刺杀,父亲受重击致死。警方觉得他过于冷静,认为他在撒谎,尽管他自称是清白的。他因此被控谋杀,在监狱里呆了17年。
而在另一桩案件中,16岁的杰弗里·德波索维奇(JeffreyDeskovic)在他的高中同班同学被勒死之后显得过于心急如焚,过于极力渴望帮助警探破案。同样,警方认为他在说谎,判了他16年监禁。
年9月7日,凶案侦探在马蒂·坦格列夫的家门口采访他。?TonyJerome/NewsdayRM/Getty
这两个人一个过于冷静,另一个过于慌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为何都会被警方视作隐藏罪恶的线索呢?
纽约市立大学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的骗术研究员、心理学家玛丽亚·哈特威格(MariaHartwig)如是说。坦格列夫和德波索维奇后来被证明无罪,他们都是一种普遍误解的受害者:人们通常认为,你可以从一个人的行为中看出他是否撒谎。无论在哪种文化中,人们都认为转移目光、坐立不安和说话结巴等行为能暴露出一个人在说谎。
实际上,经过十多年的研究,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仍然很单薄。哈特威格与人合著了一项关于说谎的非语言线索的研究,该研究发表于《心理学年鉴》(AnnualReviewofPsychology)。他说:“作为研究说谎行为的学者,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知道说谎的原理。”人们的这种过分自信导致了严重的误判,正如坦格列夫和德波索维奇所遭受的那样。哈特威格说:“测谎错误会给社会和被误判的人带来严重后果,代价十分高昂。”
心理学家早就知晓鉴别说谎者的难度会有多大。现就职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心理学家贝拉·德保罗(BellaDePaulo)于年和同事梳理了科学文献,收集了项实验,这些实验比较了人们在说假话和真话时的行为,其中包含多项可能的非语言线索,包括转移目光、眨眼、提高声音(这一行为和说话内容无关,因此也属于非语言线索)、耸肩、改变姿势以及头、手、四肢的移动。结果发现,没有一项能够指明说谎者,尽管有一些指标是弱相关的,比如瞳孔放大、声音音调的细微提高(人耳几乎察觉不到)。
三年后,德保罗和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心理学家查尔斯·邦德(CharlesBond)回顾了份研究。这些研究共涉及位观察员,他们要判断人给出的份信息的真实性。不管是执法专家,还是学生志愿者,判别真伪的正确率都不超过54%,仅仅比碰运气高一点而已。单个实验的正确率在31%-73%之间,实验规模越小,差异越大。邦德表示:“在小型研究中,运气成分比较明显。而研究规模足够大之后,运气就只能占一半。”
瑞典哥德堡大学的心理学家、应用数据分析师蒂莫西·卢克(TimothyLuke)表示,这种规模效应表明,某些实验准确率高可能纯属偶然。他说:“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更大的影响,那很可能是因为它们不存在。”
?Dribbble然而,警方却通常持不同的说法。他们认为,实验不够真实。他们称,毕竟,实验的志愿者大多是学生,他们坐在心理实验室里,根据指令说谎话或者说真话,而犯罪嫌疑人则是在审讯室里或是证人席上接受审问,两者面临的后果截然不同。
约瑟夫·巴克利(JosephBuckley)是约翰·里德律师事务所的总裁,该律所每年培训数千名执法人员进行基于行为的测谎。他说:“实验中的‘有罪之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这不是真实自然的动机。”
英国朴茨茅斯大学的心理学家萨曼莎·曼恩(SamanthaMann)从事骗术研究已经有20年了。刚开始涉足这一领域时,她认为警方的异议是有道理的。为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她和同事奥尔德特·弗里吉(AldertVrij)先是看了几个小时警方审问一名被定罪的杀人犯的录像,并从中选取出三个确定的真相和三个确定的谎言。接着,曼恩让65位英国警官看了这六段陈述,并让他们辨别真假。因为审问是用荷兰语进行的,因此警官们完全是通过非语言线索来判断的。
她说,警官们的正确率在64%,比碰运气要好一些,但仍然不够准确。正确率最低的警官都自称是依据传统的非语言线索来判断,比如“说谎者会避免眼神接触”或者“说谎者会坐立不安”。实际上,这位杀人犯始终保持眼神接触,撒谎时也很镇定。曼恩表示:“这家伙明显十分紧张,这点毫无疑问”——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的举动,巧妙避开了人们对撒谎者的刻板印象。
曼恩和弗里吉后来又进行了一项研究。这次他们让52名荷兰警官看了几位亲属凶杀案的作案者在电视新闻发布会上的陈述,凶手都否认自己的罪行,并且表现出极度悲痛的样子。警官们辨别真假的正确率没有超过50%。正确率最低的警官都认为凶手流露的感情是真心实意的。
但这意味着什么呢?曼恩说:“如果一位丈夫杀了自己的妻子,他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表现出难过,比如悔恨或者被警察抓住。非语言行为十分特殊。如果你聚焦于感情之类的非语言行为,你就会犯错。”
几年后,哈特威格和邦德在一个更大规模的实验中验证了以上结果。他们回顾了比较人们辨别高代价谎言和低代价谎言能力的研究文献。结果发现,没有证据表明,人们在识破犯罪分子或在警方调查中被错误指控的嫌疑人的谎言时,表现得比识破实验室志愿者的谎言要好。
﹡﹡﹡
无论是连环杀手还是实验室里的学生,所有这些实验中的人都大声说出了他们的谎言。年发布的一项研究中,曼恩研究了非语言类欺骗,比如试图掩盖非法行为——侦测炸弹袭击者和走私犯时接触的就是这类欺骗。她招募了52名大学生志愿者,让其中一半的人通过轮渡将一台据称含有敏感照片的笔记本从一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这些志愿者被告知要尽量融入人群,不要显得“可疑”,因为人们会试图甄别出他们。另一半志愿者则被要求运送一台普通的手机,也没有任何要他们掩盖自己行为的指示。
然后,曼恩给另外位志愿者播放了轮渡视频,要他们找出“走私犯”。志愿者们的正确率未及一半。在后来的采访中,“走私犯”说自己很紧张,但是他们有意表现得正常,用听音乐或看手机等方法让自己不紧张。
接着,曼恩加大了砝码。她重新召集了60位志愿者,让其中一半偷运一个装有俄罗斯、埃及和韩国货币的信封,而另一半则没有“走私”任何东西。但这一次,曼恩派了两名研究人员登上渡轮,四处走动,观察乘客,似乎在将他们的脸和手机上的照片进行对比。
这次一共有位志愿者试图找出视频里的“走私犯”,但正确率只有39.2%,远低于一半。曼恩说,原因是,“走私犯”故意让自己表现得正常,而“无辜者”则仅仅是自然表现。他们对突如其来的审查感到很惊讶,这在观察者看来是一种有罪的表现。
?TED-EdBlog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心理学家罗纳德·费舍尔(RonaldFisher)说,骗子可以成功隐藏自己的紧张,这一发现填补了欺骗研究中的一块空白。费舍尔是FBI特工的培训人员,他说:“没有多少研究将人们的内心情绪和其他人注意到的外在表现进行比较。关键在于,说谎者确实更紧张,但这只是他们内心的情绪,而不是其他人所观察到的外在表现。”
这些研究让研究人员基本放弃了寻找欺骗的非语言线索。但是否有其他方法来识别说谎者?如今,研究欺骗的心理学家更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