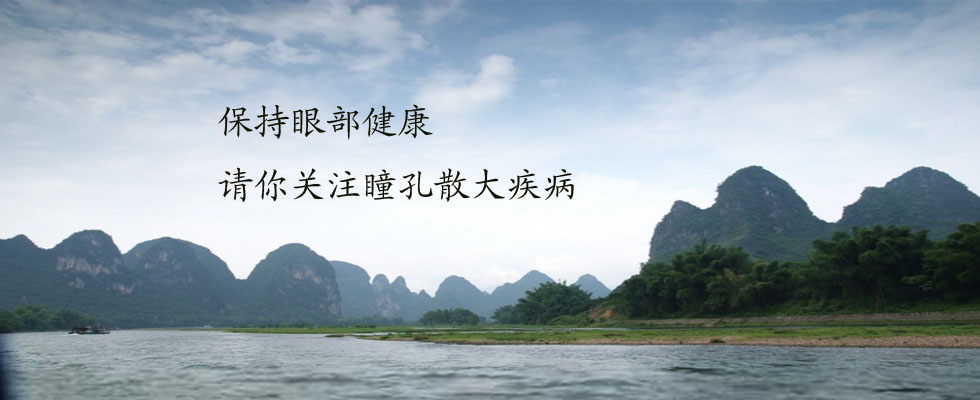祝贺
冯六一散文集《水里的光》出版发行
"冯六一,湖南岳阳人。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作品。
"水里的光文章选刊阳光不拐弯冯六一
无名巷几十年了,这条巷子还是没有名字,太熟悉,东井岭上的人忽略了给它起个名字。不过名字于它,好象也无关紧要。东井岭巷子的称谓,大多是约定俗成,有时还可以相互变通。譬如:小巷子,大巷子,弯巷子,直巷子,青砖巷子,红砖巷子,光妹子屋前,水伢子屋后,酱厂那边,学校这头。这些没有任何文化意味和关乎官衙的俗称,表明东井岭初始处于古城的边缘,没有多么显赫的身世和深厚的底蕴,仅仅是岭子上的人对这片无法在地图上标注的位置,作些特定的日常民间口头表述而已。
东井岭上的巷子,是上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聚居的老城区随处可见的巷子,幽深绵长,又相互交叉纠缠,树木生出的枝丫一样随意,显得纷乱却又自成章法。左弯右拐之后,右弯左拐;右弯左拐之后,左弯右拐,走着走着,一扇门窗或一堵院墙横亘眼前,路似乎到了尽处,你还得往前去,不经意间,又会豁然明亮,抑或坠入幽暗,——斜出一条巷子来。不熟悉的人,走进巷子就会像鱼儿窜进了洞庭大湖里的迷魂阵,转来转去,说不定又回到了现地方,似乎只能顺着一种有意无意的方向走,脚步如心思一样迟疑,自己摆脱不了自己。而熟悉的人,步态轻盈,心底油然生出自在和自信,在这里,条条巷子可以进出东井岭,处处是捷径。
当年东井岭最高建筑物是帆船社子弟学校一栋三层楼房,那势头不是鹤立鸡群,而是一条庞然的铲子船,耸立在波峰浪谷。巷子两边挤满了高低杂乱的建筑,有的是青砖瓦屋,雕刻精细花纹的木格子窗户,坚硬的麻石门框门槛,透出原来主家当年的兴盛气象;有的是杉木板房,历经风霜雨雪侵蚀,黑漆漆的,像容颜衰败的老妇人,内心安详地守望在那里;有的是新近在老地盘上堆积起来的“火柴盒子”,上端被房屋挑出的预制板所遮掩,巷子形成了方形洞穴,随形开出的窗子,乜斜着眼一样,活脱脱一个耸肩挤出来的灰不溜秋模样。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平房,墙体红砖的缝隙,白色石灰被砌刀刮出的线条,微微凹进,一层层错落开来,颇具装饰意味,这是那个简朴年代典型的建筑风格。红砖由于年岁老旧,光洁皮面有的剥落了,在厚厚的阴阴的暗光里,揣摩一番,恍若人变形的嘴唇张着,隐现对这个角落的讥嘲,又像半截话儿哽在喉咙说不出,只得露出了憨笑。
墙角跟潮湿,生出绒绒青苔,几株蛤蟆草儿巴着,顽强而无奈地呈现几片沾满灰尘的绿色。晴好天气,巷子的墙边,有时排列一队队蚂蚁,它们散发独自的隐秘气息,匆匆前行。我们从没有看到过静止不动的蚂蚁,它们总是在世间的边边角角忙碌,忙得那样平静而充实。若在阴雨天,偶尔还可以看见似乎凝滞了的蜗牛,黏糊糊的肉团,藏在硬壳里憋着的细微喘息,只有上苍遏止万物,没有任何声音,安静下来了,才能感觉得到。好像世上的重量都驮在它的背脊,那种缓慢劲,使时光沿着它的路径可以无限延伸,炫出滑湿的五彩光斑。
巷子太狭窄了,路人的视线在这里到处被遮蔽,有时无意间抬起头来,没有窥视欲望的眼睛,让那些迎面相距不过几米十几米的楼房窗口里撞来的目光,满怀狐疑。如果是熟人,会相互轻轻一笑,或者停住脚步,鸡零狗碎说道几句。普照大地的阳光被巷子切割成了各种不规则的块状,东一块西一块粘贴在地上和墙面。看到这样的光斑,我会想起旧时衣服上的补丁。现在补丁这个词不常用,衣服上的补丁也几近消失了。只有时装设计师在补丁的原始痕迹里找到了灵感,仍然怀念着补丁的质朴,把破与旧呈现为不羁和活力。
每天张着口呼吸一样,巷子不时有人被它吸进去,又有人被它吐出来。进巷出巷,往来的人把生命中漫不经心的几分几秒滞留在了这里,他们身影飘飘忽忽,虚悬在杂乱的背景上。如果细算一下,一辈子累积,那也是一段漫长的时光,面对出来的数字,我们甚至会感到惊讶。人一生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和不经意不起眼的事物纠缠在一起,仿佛填充着日常的空洞,构成了所谓的涵义。小巷每一天似乎都是以同样面目,在时光转盘上轮回,不露声色,充满了一种萦绕不散的迷惑。我们在这种迷惑滋生的浓密气息里,慢慢长大,慢慢老去。而洞悉世事的巷子却愈发显出了一种智者的旨趣,好像时刻在告诉我们:你们心里想的,正在做的那些事情,我都知道。
我见证过其中一条无名小巷的诞生。
小时候,东井岭只有两条路可以上下。岭子北面的人去东茅岭街上,得绕一个大弯,我们上学校也要围着岭子转一圈。学校操场边的红砖瓦房里,住着两个清秀文静的小姑娘,她们家后面是一块菜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几个背着书包的小家伙为了抄近道,从菜地间隙穿过,往几个不足一米高的墈下一级级跳,经常摔得裤子上沾满黄泥巴。欢快雀跃的身影是一块磁铁,孩子们的脚步都被吸引过来,时间长了,成了鲁迅先生说的,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的一条近路了。其实在许多不经意间,暗含着一种合理和一种必然。大人们也跟着走,就有人拿着锄头,把那些不足一米高的墈拔拉成一道道小斜坡,走起来顺畅多了,再不用上蹿下跳。再后来,走的人更多,又有人把它拉平扩宽,和岭下一条路连起来了。那条路经过一个水质清澈的池塘,水塘边几棵斜斜的柳树,枝条依依,轻拂水面,常常有鸟儿细细的爪子扣住柳枝,斜着身子晃悠,小小的嘴巴张合,鸣叫声玉珠子一样滚出来,溅落水中。
学校里一个姓方的老校工,我同学的父亲,他是最热心修路者之一,因为每天他的牛车从这里上下东井岭可以省不少路。我们经常看到他躬屈腰背,拿着一把锄头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填填补补,或者顺便捡些碎石铺上。我们学校是水运船工的子弟学校,两百多个孩子寄宿,父母大多在洞庭湖和长江里漂泊,只能船停靠码头装货卸货,才抽空赶到学校来看看孩子,给几个零花钱。学校整天像一个栖满鸟雀的林子,扑扑腾腾,唧唧喳喳。小学生的吃喝拉撒睡,单位安排专职保育员照顾,大些的孩子只能靠自己打理了。这么多孩子的生活物质,全靠老校工和那辆牛车。每天老校工赶着老黄牛,早上到东茅岭菜场,下午去小港粮库,往学校食堂拉蔬菜粮油,烧水蒸饭的谷壳。寒暑假期,学校里总有父母船舶远行只得留下的孩子,老校工一年四季很少见他歇息。
不知是为了提醒行人避让牛车,还是想在路途有点悦耳响声相伴,沉默寡言的老校工在牛颈上系了一个黄铜铃铛。老黄牛识路,几乎不用赶,自己慢慢悠悠迈着蹄子,踩着一种近乎固化的行进节律,那脖颈上的铜铃随着摇晃,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一串串跌落。当铃声在空旷的池塘边响起,人们就知道牛车来了,如果负载太重,岭子上会下来人帮忙推一把。
拉货时,老校工从来不坐牛车,也从来不抽打老黄牛。他手上总是捏着一根揪成麻花状的皮鞭子,象征身份的道具,跟在牛车边上走。偶尔伸出往空中摔一响鞭,不像催促牛加快步子,倒像在得意地演示自己的技艺。他经常在老黄牛背上拍拍,亲昵地骂上一句,畜生!老黄牛好像品出了其中味,回过头来,低沉地朝着老校工一声长哞。上岭坡的时候,老校工边吆喝边弓起身子在咯吱作响的牛车后面推,宁愿额头上渗出汗珠子。他把牛当作了一个朋友。每天有那么多时间呆在一起,那种眼神的交流,我想,他应该是用了真诚的心。
但老校工没有熬过老黄牛,在上岭坡的道上,推着牛车时,忽然倒下了。老黄牛在那一瞬间,死死地憋着劲拉住了笨重的牛车,没有让牛车往后倒退碾压老校工的身体,一直坚持到旁人赶来。老黄牛被人牵到学校食堂门口,卸下牛轭后,腿肚子还在发颤,也许它有一种感应或预兆,医院抢救几天后,还是死了。
出殡那天,校长领着全校师生员工站在路两边为老校工三鞠躬,然后目送那口厚实的黑棺木被老黄牛拉走了。有人看见,那天老黄牛走过池塘边时,四只蹄子迈得特别沉重缓慢。还有人说,老黄牛圆睁的眼睛流出了一串泪水,不是一滴泪水。
少年事件
随着东井岭人口兴旺,池塘被填埋了,便道修得更加平整,两旁砌起了房屋,成了东井岭的一条巷道。通往子弟学校广播室的广播线,有一节横过巷子。喜欢物理的全伢子,爬上樟树,弄一个印泥盒铁盖子吸上磁铁,接在广播线上,当起了收音耳机。只有和全伢子玩得好的人才能爬上树杈轮着来听。把铁盖子紧紧捂在耳朵上,里面传出的声音,嗡嗡叽叽,嘈杂刺耳,只能隐隐约约,断断续续,听清几句比老师说得更加标准的普通话播出的新闻,或者从头到尾激昂不已的革命歌曲。但孩子的乐趣似乎不在铁盖子里传出的内容,而是物理现象的神奇美妙。
当我们身体像巷子边的樟树一样膨胀时,既亢奋又压抑的年代里,也有反叛的个例。一个不过十四、五岁的懵懂少年,我同学湖儿的哥哥,夜晚在巷子红砖墙上,写了一句我至今也不知道的大逆之言——“反动标语”。当时是万众一心,敬仰一人,如此忤逆地发泄年少的迷蒙,抑或内心的莫名冲动,算得是惊天之举。当时如果有人看见了这样的词语,不能念出声音来,重复一次,思想会反动一次,被人听见,说不定你就成了罪人,即是心里暗自默念,不觉间也会生出罪恶感来。
早上第一个路过巷子发现标语的人,脸吓得寡白,生怕什么事赖到自己身上来,赶紧喊上邻居一起到派出所报案。得知岭子上出了大事,我去看的时候,巷子两头被带红袖章的人守着,红砖上的字迹已经用一块纯净的蓝布遮盖了,等待派出所的人来勘查。那块蓝布我还记得,不知是谁家拿来的,开满了白色长蕊低垂的菊花,蓝色的净和静,看着特别舒心,恍惚可以浸入骨子和人一起慢慢融化。
几个站在巷子里的大人面孔严峻,相互嘀咕着,谁这么大胆,这么反动!他们黑眼珠子射出凌厉的光,铁扫帚一般在巷口扫来扫去,好像拥挤在这里看热闹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温润的蓝布和冷峻的目光,让似懂非懂的我们处于一种夹缝,生怕找到自己头上来,身体紧张得有些收缩,不知所措。学校老师叫岭子上读书的孩子都写了几个字,交给派出所的民警辨认。最后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凭什么证据找到湖儿他哥哥的。两个穿蓝警服的民警将他带走时,父母站在木门边吓得瑟瑟发颤。但谁也没有想到,不知是痛恨哥哥给家里带来了耻辱,还是想表明和他划清界限,湖儿在哥哥的屁股上踢了一脚。凭着这一脚,湖儿得到学校的表扬,臂膀上箍上了红小兵的袖章。
语言很不恭,当然,后果很严重。学校是由“工人宣传队”主事,食堂就是礼堂,湖儿的哥哥跪在食堂饭桌搭起的台子上批斗一番后,被学校开除了。没有书读,他整天无所事事,到处游荡,邪恶勃兴,要报复处理他的“工宣队”队长。当时单位在东井岭上为船工家属办了一家芦席厂,每家每户锤芦苇编苇席,房前屋后堆满干枯的芦苇捆子。他跑到队长家的屋后,悄悄划燃了一根小小的火柴。仅仅是枯黄苇叶堆上一点火苗,还没有来得及找到燃烧的方向,还没有感受一点灼热尖锐的快感,就遭遇了清冷冷的水。那个年代,也许是人心弦绷得紧紧的,相互不信任,充满了怀疑,人的细微表情,话语情绪,肢体动作,都会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