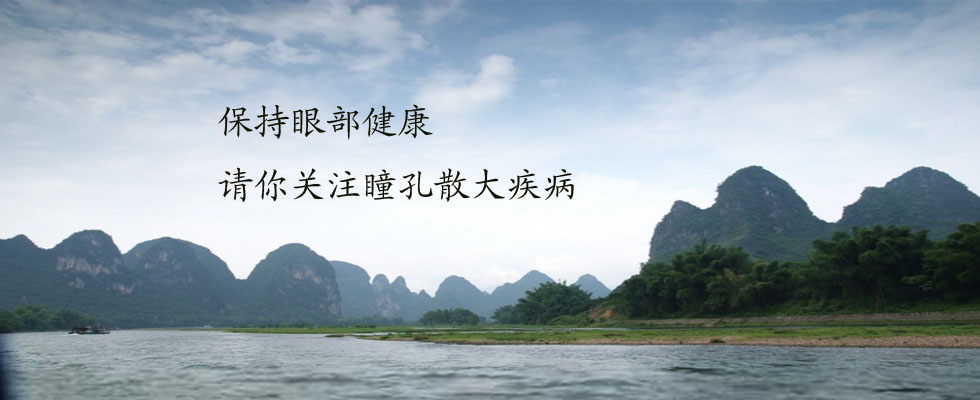二十年前高海平曾出版过一本散文集;其中写女儿的那组亲情类散文,以及那篇伫兴而就的抒情之作——《一只驳船》,迄今仍不失其性灵翻转的绝对参照。
多年来拜读他的散文大作,我总情不自禁地两厢对读,以期明确他的感情泊地吟哦的来路去向;有所逾越,窃喜,视同己出;漫与、敷衍、面目可憎者,实言相告,忿忿不已。
一忽间我们都到了知天命之年,而他又有第二本散文集面世;多数熟悉的篇什相继一一过目,一些迂执之念有所松动,迄今依然感奋的判断如鲠在喉,我自信我对他的散文修为还是别有意会的。他写他的,我说我的;文事相契,和而不同,卅年来我们不正是这般平平淡淡地走过来吗?有关高海平的散文,我有我的思考;甚至有时比他本人体味得还要细微。
譬如他对山水徜徉的回体味和记述。
曾有朋友调侃他的摄影及其相应的文字;认为后者不及前者。他深以为是,笑而不语。
当时他反应得意的表情打动了我,我禁不住感叹户外“行走”之于他寻常日子打发的重要性,更是意识到,他廿年散文跋涉的主要的引擎,或许正受益于此。
在他女儿还牙牙学语时,赶上了中秋节;山路迢迢,朋友爽约,他只好带着姑娘坐客车回乡宁的老家。到家后,他向姑娘回忆他幼年生活状况,他姑娘却天真地诘问:她妈妈当年住在哪眼窑洞?他无语,所以才有了《带女儿回家》(——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就以该篇命名的)深情的瞩望。
亲情与乡土就这样奇妙地对位,分明显示了他在“异乡”拼打的诸多不适。
一个农人的后裔面对大时代变动不居的处境,着实无从复返“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所以他要“形而上”地去克制、抵御,将之被动形塑的人生延迁的必然事态纳入主动迎接的体味,从这个意义上看,“自我”在路上的人生奏鸣为是唱响、做大,看似闲暇,旅游观光般恣意,实是行者无疆,用遍历一切的生活姿态,安顿“爱”与“自由”龃龉下的诗性。
这无疑像他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所称呼的那样,属于“孤独的浪漫”;带着这般行走的意志,依旧在亲情与乡土间穿梭的他,继续寻找栖息之地。
供他开垦的感情领域,杂沓,缭乱,却很协整,似乱石铺街,如渔舟唱晚,看不到这层联系则很难体会他多管齐下的腕力所在。我欣赏他的这份情怀,一如他兀自拙朴的坚守。
《母亲的礼数》所以写得那般扎实。
《宁静也是一种声音》所以显得格外的飘逸。
与我推崇的《一只驳船》相比较,我注意到海平形塑感情对象的“空间化”取向先后幻化明显。据其自述,“驳船”云云受益于当年取道某地返乡必须途经汾河的具体感知。“一桥飞架南北”,曾经助渡的器物被废弃,经年孤零零的泊在汾河的一边。
他为是有所悟。当年他对老子的“无乃为之有用”的哲思颇有心得,至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观念尚未亲炙,可我觉得他的这篇抒情小品,通体散溢着犹如海氏针对梵高的《鞋》所发挥的诗性的智慧。
如同所知,海氏就伦常“时间性”的维度开启了存在诗性领会的意象,把“思”和“言”的源初一致性用“诗”来统领,所谓的澄明之境的敞亮,不消说也是“空间化”创生遗迹。
海平写母亲,不独是孝心的殷勤告白,更是把作为“人之子”被恩宠的那份温馨体贴得格外亲切,居家生活的“礼数”所以在母爱的层层包裹和缓缓绽现时熠熠生辉。
如果非得以亲情来命名作者行文笔调处处聚精会神“凝眸”的这个境界,我只想说海平的感情寄托犹同由一串串明珠的连缀,虽然不是星空那般浩瀚或深邃,可也彻耀静夜的暗,为倦于远游的行者檫亮眸子。
相形之下,《宁》发挥了又一种想象,开辟出“聆听”的姣美的界域,显示了海平散文写作的新的可能。
《宁》从文体上看属于“书评”。不过他从“书评”对象那儿获得的感悟,毋宁带有“吾道不孤”的共鸣;他的高度主观化的表述,是靠着他的从容的笔调进行明澈的转喻式的申说,绘声绘色,如沐春风。
行文尤其调皮,似学子放榜之际发出惬意的笑;毕竟他所关爱的对象和他有着相似的散文情怀。他从对方的散文的成就中无疑看到了自我的不凡,回想到了自己经年跋涉的足音。
这份写作的甘苦唯有坚守着所能神会。所以他肯定“宁静”,把它当做“一种声音”来看待,然后再欣然前往。
他的第二本散文集题名为《一抹烟绿染春柳》(北京日报出版社——.7),显然是其无止境“寻找”的暂时性寄托;待他发现的精神的高地,不致让他噤声无语的。
高海平,语文报社副社长。
北京治疗白癜风最好的专家北京哪个医院白癜风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