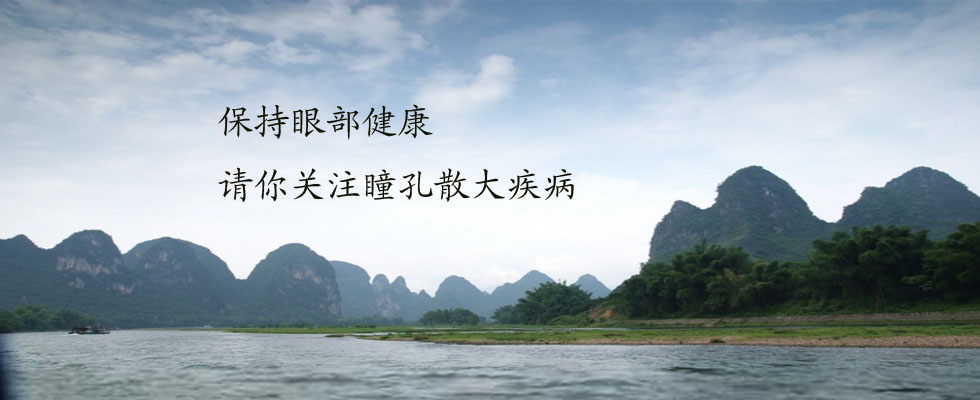多少走进又走出了两岸的胡杨林
我不能不想起一个人,他叫钱宗仁。
钱宗仁生于湘乡东郊乡茅浒洲。他开荒种树,先后在《新疆文学》、《新疆日报》、《阿克苏报》上发表文章。他遭遣返又被送回新疆。他挨批斗、遭游街甚至酷刑。还在年底,他利用字典和废纸研究汉字结构,创造出汉字笔顺号码排字法。
他本分、勤奋、纯洁,只为实现“为祖国四化建设尽力”之梦,历经坎坷坚持自学,却三次被拒之大学门外,甚至连在家乡都无法生活下去。
在他一次次遭受拒绝后,是阿拉尔接纳了他——年12月31日来到塔里木农垦大学报到。
年4月,上海《文汇月报》第4期发表了《胡杨泪》,介绍了钱宗仁二十年的艰难曲折不屈不挠坚持不懈奋发图强的历程。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锐看过以后,忍不住立即作文向《人民日报》推荐,《人民日报》登出之后,全国各大报纸30多家相继转载,全国千千万万的读者无不深受感动。钱宗仁也因此于年3月被借调入《人民日报》当记者。10月,因肝癌晚期逝世,终年仅41岁。
他的一生悲怆悲凉悲壮,是一个成功者,更是一个失败者。
他一生的苦难命运浓缩了新中国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的命运。
他的一生折射了共和国的苦难历程。
《胡杨泪》的作者《人民日报》社的记者孟晓云获得线索来采访,并不顺利。从阿克苏到阿拉尔塔里木大学公里,交通工具让孟晓云表示“如果实在没有车,我就走到阿拉尔……”同样,阿拉尔以超人的热情接纳了孟晓云,让她写出了影响全国的佳作。
《胡杨泪》中写道:
人生,有辛酸,有劳苦,也有人的创造和热力,有污浊,更多的却是人性的光彩;这里,有痛苦,也有克制、忍耐,更多的是自我牺牲中所获得的创造的欢乐。
钱宗仁的身上印着过去的痕迹,也包含着未来的种子,不仅整个脸,而且整个姿态,都表现出思想、热情和生命的波动,你能听见他汹涌的内心的呼声。
他的经历,他的性格,他的人品,他的精神,都使我想起塔里木河畔的胡杨,那会流泪的树。
钱宗仁就是一棵扎根在阿拉尔的胡杨,一个曾被忽略的倔强的灵魂。在沙漠旱风的席卷和盐碱的吞噬中,那被压抑、被扭曲的人性终究要伸直他的躯干。他不抱怨,不灰心,因为,他知道以往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不幸,冬天过去了,他正和人民和国家一道共享春风的吹拂。
《胡杨泪》托物咏志,以胡杨类比钱宗仁,上述华彩文字想必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鸣。
那么,现实中的胡杨究竟是怎样的树?深藏着怎样的秘密?又预示着怎样的天机,给人怎样的启迪?
让我们去阿拉尔的睡胡杨谷探访领略吧!
在阿拉尔境内的塔里木河两岸保存着世界目前面积最大、最完整、形态最奇特的‘原始’胡杨林。
下了国道,但见荒漠如海,天似穹庐,辽远深邃,雄浑苍凉;沙丘如潮如象,奔腾翻卷。路像从远古飘来,左突右冲,七拐八弯,时隐时现,若有若无……阳春三月,与路相伴的湿地和湖泊冰雪消融,沙鸥和天鹅自由游弋、潇洒翱翔。
行驶大约8公里,豁然开朗……目光掠过齐人的芦苇荡,夕阳下,莽莽苍苍,像万众齐跳霹雳舞,似万马驰骋,又像火焰奔突狂飙。
走近,树,一个个都赤身裸体,奶灰色的一片,与天空构成凝重的和谐。直立、斜刺、横卧,各具形态,争奇斗异。状如雄鹰展翅,像张牙舞爪的白骨魔女,又似一堆骷髅,又象虎狼在咆哮;有的似披坚执锐的武士,威武不屈,虽死倚剑而立;又似白衣少女掩面垂首如泣如诉;有的像飞天飘然起舞,婀娜多姿;有的状如老妪盘腿席地絮叨身世;有的如利剑直刺天空,大有与天空俱残同碎的气概……岁月把它们定格成永恒,凝固成冷峻的沉默。
偶有风掠过,砂砾相撞,枝桠震颤,如婴儿啼哭,如少妇哀怨,如鬼哭狼嚎,如箫笛浅吟……
太阳即将下沉,逆光进入镜框的胡杨有的像屈子在引颈翘首怒问天空;有的像天狗张着大口吞噬夕阳;相距不远的两株,枝桠挣扎着,像一对被迫分开的情侣,那种执着、忠贞和无奈……也是相距不远的两株,巍然矗立,“相看两不厌”,真情守望着共同的梦……还是两株,一株赤裸,一株皮厚如龟甲,斜伸的躯体,叠压胶着,演绎摄魂的生死恋……
资料显示,胡杨是第三纪残遗的古老树种,能够在沙漠中生存并天然成林,距今已有万年以上的历史;世界范围内,胡杨主要生长在中国新疆的塔河流域,绿色长廊两千多公里,雄伟壮阔。
专家称此地为“塔里木原生胡杨标本库”,摄影家称此地为摄影的天堂,雕塑家称这里“天然的雕像群”,油画家说“活脱脱质感强烈的油画”;诗人说“到这里感受生命和力量的震撼”……
活着的胡杨夏绿秋黄,固然旖旎;死去的胡杨更加壮美,以独有的形态,给人思想的启迪。
只有躯干、没有树皮和枝叶——虽睡犹醒,虽死犹生,故得名‘睡胡杨谷’。
“睡”表明在休憩,在思考,在期盼,在酝酿,在积蓄,在修炼,在补充,在造势……
睡胡杨谷坐落在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和田河和克里雅河古道交接处,克里雅河断流、和田河改道,胡杨集体逐年干枯。尼雅古城、圆沙故城和昆岗先民家园以及下游楼兰古城消失,史学家一致认为水消失是主因,这片胡杨林成为无言的佐证。
半个世纪前,一师阿拉尔市大举开发塔里木,到这里嘎然而止,严加保护,完整地保留至今,成了当今生态文明建设的教科书和警示牌。树木构成独特:密度大,一棵挨一棵;大小层叠,有古老的参天大树,也有次生小树,间杂其他类型的树,别于塔里木河流域其他地区的胡杨林,具有更高的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
这片虽死犹生的睡胡杨,有四万多亩。
阿拉尔境内的塔里木河两岸,迄今仍然完整存留着活着的原始、次生胡杨林,加上人工栽种的,几百万亩。
阿拉尔曾是丝路驿站。相传,公元前60年前后,郑吉将军被派遣在渠犁(今为库尔勒一带)屯田,领护当时“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号称“西域都护”。
郑吉率部从今轮台出发巡查。过沙雁州(沙雅)进入昆岗(阿拉尔)地界,看到茂盛高大的胡杨林一望无际,很是好奇。向导告诉他,当地人叫胡桐树(胡杨),因其耐寒、耐热、耐碱、耐涝、耐旱,又被称为“英雄树”。
郑吉哈哈大笑,脱口道:“英雄胡桐树,从此归汉家。”
郑吉是首任“西域都护”,史学家普遍认为从郑吉开始,历史上才真正实现了中原王朝对西域实际管控的抱负。当地人为了纪念郑吉,叫这片树林“刘家胡桐”。
多少年来,在阿拉尔流行一种说法,“活着,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下,一千年不烂……”
三个一千年。
三千年。
——出此豪言的人,年龄迄今一定远大于三千零一年,否则怎知胡杨的三个一千年?
阿拉尔人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语言的丰富不比身边塔克拉玛干的沙粒少。当语言不足以准确表达感情时,只好借助于夸张——由此可见阿拉尔文化的一斑:崇尚英雄,敬重坚强,拒绝平庸,追求永恒。他们自喻为胡杨,所以,他们坚信不疑胡杨有“三个一千”。
哦,胡杨树,英雄树,壮美的树!
塔里木大学坐落于阿拉尔市东南角,距离塔里木河不足一公里。其被包围在胡杨林中,堪称世界唯一与胡杨最亲近的大学。该大学对于胡杨的研究,在世界学术界居领先地位,地缘优势得天独厚。
年国庆节期间,时任国家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召集第一师的领导赴京,汇报对塔里木的勘察规划,并亲自主持召开农垦部党组会议,认真审查了塔里木开发规划蓝图。然后,农垦部作出了“关于开发塔里木、向沙漠进军”的决定,由此拉开了声势浩大的塔里木开发会战序幕。
塔里木开发大会战伊始,王震即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敏锐地意识到,塔里木屯垦事业繁荣发展,要依靠文化和科学技术,离不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有技术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当时全国各地普遍缺乏专业人才和管理干部,仅靠国家从内地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中调配,显然是杯水车薪,远远无法满足需要。
“我们可以就地取材、就近培养嘛!我建议由第一师在阿拉尔垦区筹办一所农业大学。”王震仍然挥舞惯常的将军手势,对新疆兵团的战友们说。
遵照这一指示,第一师经过反复论证,并报经农垦部、新疆自治区党委、新疆兵团党委批准同意后,于年10月15日正式创办大学,当时取名叫“塔里木河农业大学”。
于是,塔里木河岸茫茫荒原上从古至今开天辟地,有了第一所高等学府。
还在西北人民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凯歌频传向新疆挺进的路上,王震就在开始考虑进驻新疆以后要做的工作。在和大家聊天时,王震炯炯有神的双眼扫视着眼前的精兵强将,剑眉一扬说:“同志们!我们解放大西北是为了什么,党中央号召我们进军新疆又是去干哈?是去享福,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做国民党政府那样的接收大员?不是,根本不是!我们去干什么?毛主席曾指示我说,‘你们到新疆的主要任务是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你们要以替历史上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统治者还债的精神去那里工作。’新疆有几个英国大,有几百个南泥湾大,进军新疆、建设新疆,大有可为!我们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办事,办好事,既要保卫边防、巩固治安,又要率领各族人民,并肩战斗,大搞建设!”
搞建设离不开人才,离不开读书人,王震深谙此道。在挥师挺进新疆的路上,部队像蜜蜂一样,只要是蜜就采进巢穴,只要是花粉就揽到怀里;遵照王震的指示,不管小学生还是初中生,不管文科生还是理工生,不管男还是女,凡愿意参军的一律都招录入伍。
塔里木河农业大学创办之初,教学基础设施仅有几顶帐篷、六个地窝子、五间土平房和已开垦出的亩耕地;师生们在边学习边建校中制作了简易课桌;其教学和管理骨干,都是当年部队一路招收的学生兵;学校仅办有农业经济、农学、水利、农机、会计统计五个班;首批名学员来自第一师各单位选送的基层干部、转业军人和劳动积极分子,实行半耕半读。
20世纪60年代,王震曾六次视察新疆,有四次视察了塔里木和塔里木河农业大学。
在共和国最困难的岁月里,在反冒进中,许多大专院校相继下马。塔里木河农业大学也被以“不正规、条件差”为由,要求下马。
“我们要把眼光放远点。没有大学,没有科研机构,塔里木怎么发展呢?至于说不正规,可以慢慢正规起来;条件差,可以慢慢改善。你们不仅不能下马,还要扩大招生,要到内地去招生。”王震对塔大的干部说。
“我来兼任你们的校长,我帮你们克服困难。回到北京,我要向总理、向总司令报告这件事。”
就大学名称问题王震一锤定音:塔里木农垦大学。他说:“‘农业’两字有局限性,你这个学校不能只培养农业技术人才,还要培养其他方面的人才。”他建议将“农业”改成“农垦”,并挥毫题写了“塔里木农垦大学”,简称“塔农大”。放下笔,他又说:“我们的农垦事业是综合性的事业,应培养多方面的人才,同时‘农垦’两个字,也意味着要艰苦奋斗嘛。”
随后,王震饶有兴致地察看了师生们建造的校舍和开垦的试验田,高兴地说:“当年在延安,抗大的学生进校先挖窑洞,你们的学生进校先盖土房,这就是延安精神。”
“在特殊的时期,在特殊的地方,用特殊的办法创办的特殊的大学”,一个凝铸寄托部长心血和理想的大学,一个由师生自己动手挥汗建起来的大学,一个远离城市崛起于农田的大学,一个把“抗日军政大学”搬到塔里木河边的大学(年、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长篇通讯都以《今日抗大》为题的报道了塔大。)……
而今,培养了数万把希望的田野带到21世纪人才的大学,一个成长起数千带领众人建设新型城市干才的大学,一个最集中连片占据新城阿拉尔市三千多亩地的大学,一个三次更名确立为“塔里木大学”的大学,一个有10个学院、4个一级学科硕士点、涵盖19个二级硕士学位专业点、46个本科专业、涉及8大学科门类、4个省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的大学,一个距离新中国首都北京最远却被列入国家“计划”的大学……
一个没有大学的地方,其窘迫不言而喻;一个没有精英的地方其尴尬,也不难想见。
阿拉尔在接纳钱宗仁之前之后的各个时期都产生了世人瞩目的精英。
当时,国家要前无古人地在高纬度无霜期短的天山北麓种植棉花。年,刘学佛在玛纳斯河畔精心栽培的1亩棉花创造了亩产籽棉.5公斤的旷世纪录。其后,又在该流域创造了大面积棉田丰产纪录。年在第一师沙井子垦区继“胜利一号”“胜利二号”之后培育出棉花新品种“胜利三号”。
陈顺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育成新中国第一个优质、早熟、丰产的“军海一号”长绒棉,成为六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中国国用、出口最多的长绒棉。
李尔文大学毕业后,人生第一站坐落在塔里木河源头之一的喀什噶尔河边第一师三团。他调到塔里木河上游北岸第一师农科所的十多年里,培育出“新海13号”、“新海15号”、“新海21号”三个长绒棉品种和“新陆中7号”、“新陆中14号”两个陆地棉品种,被誉为“长绒棉之父”。他的长绒棉品种在上世纪90年代迄今,成为中国国用和出口最多的长绒棉。
如果说刘学佛、陈顺理和李尔文在中国农业的棉花科技领域勇攀高峰赢得举世瞩目的光荣,那么,近五万从黄浦江边走来的支边知识青年,润物细无声地致力于文化知识普及,让西部边陲这一方水土文明程度大大提升,就正如年胡耀邦在第一师考察后为支青题词赞美的:“历史贡献与托木峰共存,新的业绩同塔里木河长流。”
年——年,十万上海支边知识青年来到新疆,分配在第一师阿拉尔近五万。初来乍到,姑娘水灵,却掩不住纤弱;小伙英俊,却遮不住单薄。当塔克拉玛干沙漠上空的太阳照射,当塔里木河的风吹拂,喝了阿拉尔的咸水吃了塔里木的玉米馍,短短半年,姑娘肤色和塔里木的胡杨接近,褐里透红,体格丰满结实起来;小伙皮肤变糙像胡杨躯干的表面有褶皱,嘴唇上和两腮长出了胡须,胸背臂的肌肉隆起像蒜头堆积,健壮如牛;尤其拥有文化知识,通过面容和形体透出来的气质、磁场,姑娘聪灵妩媚,小伙睿智潇洒。他们中人才济济,文理科、文学艺术(舞蹈、美术、表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吹拉弹唱琴棋书画等,各路人才无所没有。他们一举手一投足,高雅;一颦一笑一说一唱,有情调。姑娘心灵,任意一块布料经他们裁剪出来,穿到身上都让人感到得体看着舒服;小伙手巧,随便一截木头,七锯八刨就成了一件精致的家具。我的同龄人小学得益于上海支青的启蒙教育,中学以及高中,受惠于上海支青的提升,很多人踏进高等学府,不曾离开上海支青甘当垫脚石般的辅导和激励……
有个诗人年轻时从阿拉尔走到广州成为电视编导,曾写下诗行:我属于南方,我属于北方——我的根在阿拉尔……
到阿拉尔采风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有位著名作家说,走进或者走出塔里木河两岸的胡杨林,身上很自然地被植入了三五九旅的革命基因,五湖四海的文化基因,碰撞裂变,爆发出的才智胜过核能量。
井冈翠竹来到南泥湾长出鲜花,在塔里木的胡杨林里高举人类文明的大旗和民族魂。
三五九旅人——塔里木人——阿拉尔人。一代一代,犹如塔里木河水滔滔流淌绵延不断,生生不息。
我的故乡是阿拉尔。
塔里木河从阿拉尔穿过。
(编辑:卷卷文:天然终审:李沙平)
北京哪里的白癜风医院好儿童白癜风怎样治